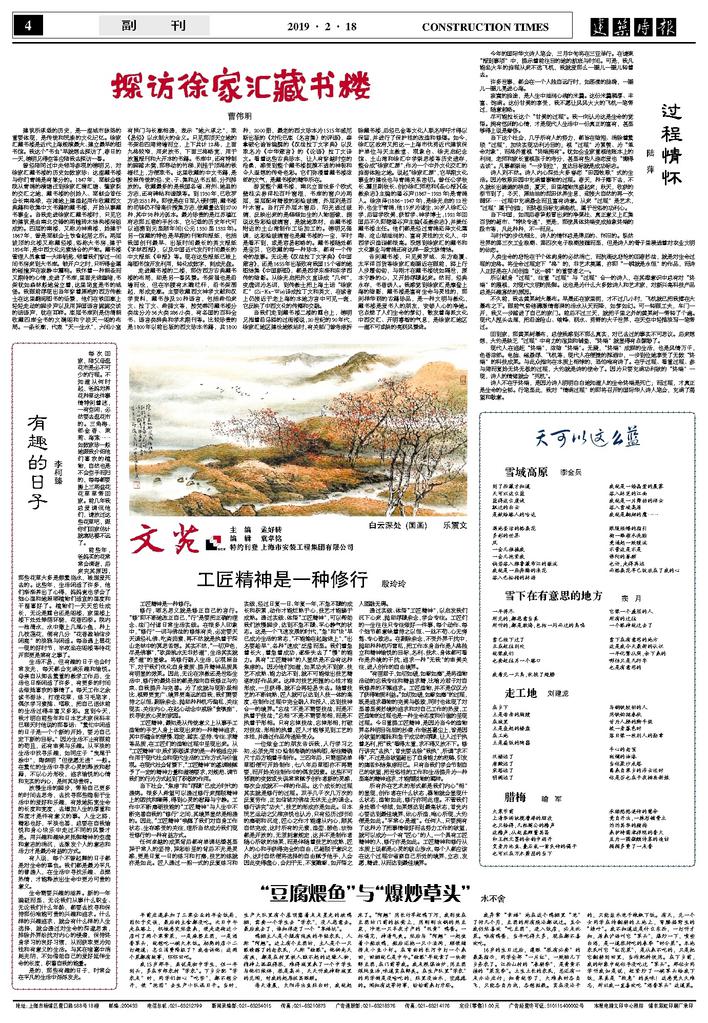年前应邀参加了三家企业的年会饭局,因忙于交谈,最后的主食都没吃。次日中午走在路上,饥饿感突然袭来,便走进街边小店叫了两个家常菜,一是麻婆豆腐,一是酒香草头,就想吃一碗大米饭。相熟的店小二打趣道:怎么消费降级了?我告诉他:这两个菜都有故事,怀怀旧吧。
我15岁那年,虽说是初中学生,但一年到头,多在市郊农村“学农”。下乡分配“学农点”时,同学们担心“吃苦”,都不想分开,便“抱团”去生产小队混日子。当时,生产大队里有个屋顶露着点点星光的破鸭棚,需要一个学生去“学农”,没人愿意去。最后我去了,谁知掉进了一个“享福坑”。
鸭棚主人是个腿有残疾的年轻农民,人称“阿翘”。边上有个豆腐坊,主人是个一只眼睛瞎了的老农民,人称“独眼”。他俩先天有疾,都是在村里被人瞧不起的边缘人物,精神上孤寂得很,难得城里来了一个中学生与他们做伴,很是高兴,天天听我神聊城里的见闻,对我的起居极其照顾。
每天清晨,太阳浮出鱼肚白时,我就起床了。“阿翘”用长竹竿赶鸭下河,我则坐在豆腐坊门前的板凳上,用刚刚出锅的热豆浆,冲泡一只半夜才产的“双黄”鸭蛋。一杯喝完,神清气爽。然后与“阿翘”一起坐着小船放鸭,船后还拖一只小渔网,顺便捕捞点小鱼小虾。在弯曲的长河中打一个来回,回棚就已是中午。“独眼”早就拿了一块新鲜豆腐,在门前等我。我点燃煤油炉,用豆腐煨炖鱼汤,味道实在鲜美。在生产队里“学农”的同学倒是没啥吃的,肚里没油水,空瘪瘪的。闻知有这等好事,纷纷前来打牙祭。
我异常“幸福”地在这个鸭棚里“泡”了好几个月,豆腐的所有烧法都试过。至今我仍然喜欢“吃豆腐”,进入饭店,必点此菜。唯有鸭蛋,当年吃得太多,现在都不喜欢吃。
16岁的生日过后,遵照“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同学全部“一片红”,一股脑儿下乡务农了。江西山村的“春耕季”,是青黄不接的“菜荒季”。土生土长的农民,总还有一点办法应付;知青就苦了,大难来时各自飞,只能各自为战,各想招数。实在没法子的,只能盐水泡干辣椒下饭。有天,见一个女同学在待翻耕的土地上,弯腰掐野生的“绿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打听才知,原来沪语叫它“草头”,爆炒一下,喷些白酒,是一道很好吃的春季“时令菜”。本地农民叫它“红花菜”,是从来不吃的,只是把它翻耕到田里,当作肥料使用。在下乡前,我的印象中就似乎没吃过“草头”。那位女同学听我如是说,赶紧炒了一碗草头给我下饭,果真是“救急”的美味!这感觉久久难忘,所以我一直喜欢吃“酒香草头”这道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