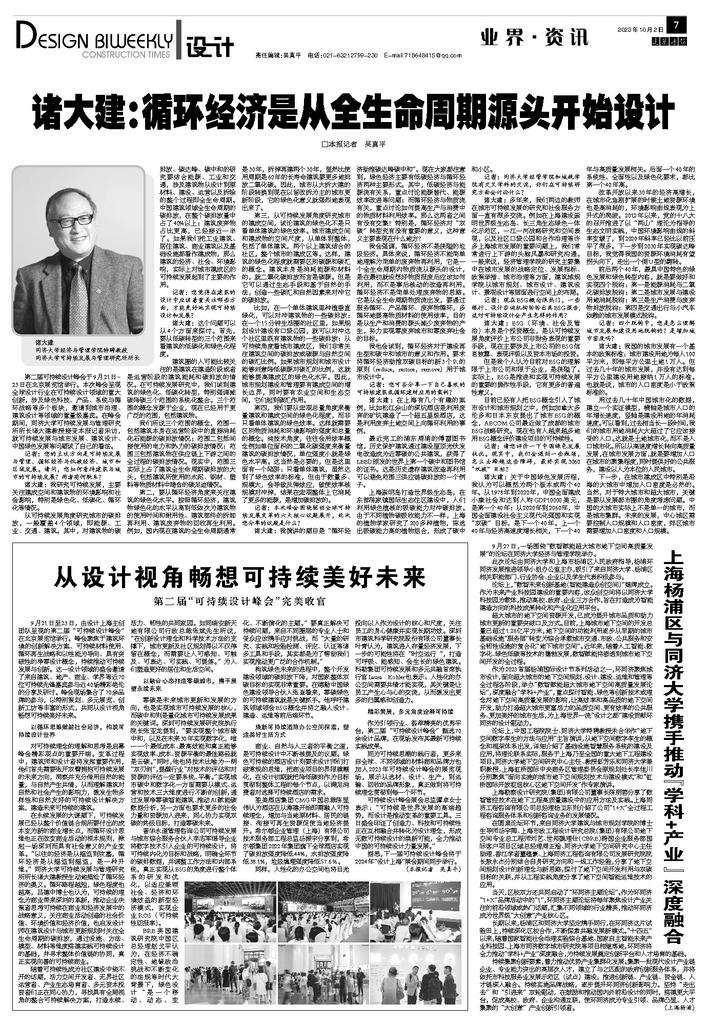第二届可持续设计峰会于9月21日-23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本次峰会呈现全球设计行业在可持续设计领域的重大创新,涉及绿色科技、产品、系统与循环战略等多个板块,邀请到城市治理、建筑设计等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在峰会期间,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发展、建筑设计、中国绿色发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您的主攻方向是可持续发展与管理、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城市和区域发展。请问,您如何看待建筑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两者有何联系?
诸大建:我研究可持续发展,主要关注建成空间和建筑物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特别是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等情况。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城市的碳排放,一般覆盖4个领域,即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其中,对建筑物的碳排放、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要结合能源、工业和交通,涉及建筑物从设计到原材料、建设、运营以及拆除的整个过程即全生命周期。中国建筑领域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在整个碳排放量中占了40%以上;建筑废弃物占比更高,已经接近一半了。如果我们把工业建筑、居住建筑、商业建筑以及基础设施都看作建成物,那么建筑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实际上对城市建成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记者:您觉得在建筑的设计中应该着重关注哪些方面,才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设计和发展?
诸大建:这个问题可以从4个方面来探讨。首先,要从低碳转型的三个范围来看建筑的低碳化和绿色化程度。
建筑圈的人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建筑在建造阶段或者是运营阶段的建筑能耗和碳排放的情况。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我们谈到建筑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特别强调减碳降碳三个范围的系统化整合。三个范围的概念发源于企业,现在已经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包括建筑物。
我们所说三个范围的概念,范围一包括建筑本身在运营阶段中的直接消耗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情况;范围二包括间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的碳排放情况;范围三包括建筑物在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全过程的碳排放情况。现实中,范围三实际上占了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大头,包括建筑所使用的水泥、钢材、塑料等物质材料中隐含的碳足迹情况。
第二,要从循环经济角度来关注建筑的绿色化水平。按照循环经济,建筑物绿色化的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建筑物的使用时间和耐用性、建筑部件的拆卸再利用、建筑废弃物的回收再生利用。例如,国内现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通常是30年,拆掉再建两个30年,显然比使用周期是60年的长寿命建筑要更多地排放二氧化碳。因此,城市从大拆大建的阶段转换到现在以留改拆为主的城市更新阶段,它的绿色化意义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第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城市的建成空间,谈论建筑的绿色化不是只看单体建筑的绿色效率。城市建成空间和建成物的空间尺度,从单体到整体,包括了单体建筑,两个以上建筑结合的社区,整个城市的建成区等。这样,建筑的绿色化程度就需要区别碳源和碳汇的概念。建筑本身是消耗能源和材料的,就二氧化碳排放而言是碳源。但是它可以通过生态手段和基于自然的手法,创造一些碳汇和自然因素来对冲它的碳排放。
比如,在一个单体建筑里种植垂直绿化,可以对冲建筑物的一些碳排放;在一个15分钟生活圈的社区里,如果规划设计建设有口袋公园,就可以对冲这个社区里既有建筑物的一些碳排放;从可持续角度看城市建成区,我们非常关注建筑空间的碳排放或碳源与自然空间的碳汇比例。如果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能够刻意降低碳源对碳汇的比例,这就能够提高建成区的绿色化水平。因此,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要有建成空间的增长边界,同时要有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它们起到碳汇作用。
第四,我们要从宏观总量角度来衡量建筑和建成空间的绿色化程度,而非只看单体建筑的绿色效率。这样就需要区别物质消耗和环境影响的强度和总量的概念。纯技术角度,往往会用效率概念例如单位面积的二氧化碳强度来衡量建筑的碳排放情况,单位强度小就是绿色水平高。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陷阱:只看单体建筑,虽然达到了绿色效率的标准,但由于数量多、规模大,会导致反弹效应,致使效率被规模对冲掉,结果在宏观整体上它消耗了更多的能源,是增加碳排放的。
记者:本次峰会围绕驱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变革的六大核心议题展开,此次您分享的议题是什么?
诸大建:我演讲的题目是“循环经济助推碳达峰碳中和”。现在大家都注意到,绿色经济主要有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两种主要形式。其中,低碳经济与能源流有关系,重点讨论能源替代、能源效率改进等问题;而循环经济与物质流有关,重点讨论如何提高生产与消费中的物质材料利用效率。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交集?特别是,循环经济对“双碳”转型究有没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会强调,循环经济不是狭隘的垃圾经济。具体来说,循环经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简单的废弃物再利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内物质流从源头的设计,是在最初就设想好物质报废后应该如何利用,而不是事后被动的改造再利用。循环经济不是简单处理废弃物的思路。它是从全生命周期物质流出发,要通过服务循环、产品循环、废弃物循环,多循环地提高物质材料的使用效率,目的是从生产和消费的源头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努力实现零废弃城市和零废弃社会的目标。
我也会谈到,循环经济对于建设再生型和碳中和城市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将循环经济助推双碳目标的新3个R的原则(reduce,restore,remove)用于城市设计中。
记者:您可否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可持续建筑或循环建材应用的案例?
诸大建:在上海有几个有趣的案例,比如松江佘山的深坑酒店是利用废弃的矿坑建造了一个超五星级酒店,这是利用废弃土地空间上向循环利用的事例。
最近完工的浦东周浦的傅雷图书馆,历史保护建筑通过建设屋顶光伏发电改造成为近零碳的公共建筑,获得了LEED颁发的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图书馆的证书。这是历史遗存建筑改造再利用可以避免范围三供应链碳排放的一个例子。
上海崇明岛打造世界级生态岛,在东部陈家镇国际生态住区建设中,人们利用绿色植被的吸碳能力对冲碳排放。由于不同植物碳吸收能力不一样,上海的植物学家研究了200多种植物,筛选出吸碳能力高的植物组合,形成了碳中和小区。
记者: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和城规学院有交叉学科的交流,你们在可持续研究方面会讨论什么?
诸大建:多年来,我们两边的教师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一直有很多交流。例如在上海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一江一河战略研究和空间表现,以及社区口袋公园和合作治理等许多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我们常常进行上下游的头脑风暴和研究沟通。一般来说,经济管理学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指标、政策举措、城市治理等方面,建筑城规学院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层面进行空间上的布局。
记者:现在ESG概念很热门,一些银行、设计咨询机构纷纷出具ESG报告,这对可持续设计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诸大建:ESG(环境、社会及管治)本身是个投资概念,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评价上市公司非财务表现的重要手段,现在主要涉及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表现评级以及资本市场的投资。
但是我个人认为目前对ESG的理解限于上市公司和限于企业,是狭隘了。实际上,ESG是推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操作性手段,它有更多的普遍性意义。
目前已经有人把ESG概念引入了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之中,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和日本东京提出了城市ESG的概念,AECOM公司最近做了成都的城市ESG战略研究。现在也有人越来越多地用ESG概念评价建设项目的可持续性。
记者:请您评价一下中国绿色发展状况。现实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瓶颈,怎么去跨越这些障碍,最终实现3060“双碳”目标?
诸大建:关于中国绿色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两个版本或两个40年。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达到人均GDP10000美元,是第一个40年;从2020年到2060年,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双碳”目标,是下一个40年。上一个40年与经济高速度增长相关,下一个40年与高质量发展相关。后面一个40年的系统性、全面性以及绿色化要求,都比第一个40年高。
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高增长,在城市化急剧扩展的时候土地资源环境也是高消耗的,环境影响曲线表现为上升式的爬坡。2012年以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推进了以“两山”理论为指导的生态文明实践,中国环境影响曲线的斜率变缓了,到2020年斜率已经比以前压平了很多。下一步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我觉得我国的资源环境消耗有望拐头向下,走出一个倒U型的翻转。
前后两个40年,最具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和绿色转型内容,就是要做好和实现四个脱钩:第一是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第二是城市发展与建设用地消耗脱钩;第三是生产消费与废弃物排放脱钩;第四是交通出行与小汽车依赖的城市发展模式脱钩。
记者:四个脱钩中,您是怎么理解城市发展和建设用地脱钩的?是增加城市密度吗?
诸大建:我国的城市发展有一个基本的政策标准:城市建设用地为每人100平方米,即每平方公里土地1万人。但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发展,并没有达到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接纳1万人的标准。也就是说,城市的人口密度是小于政策标准的。
用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的数据,建立一个实证模型,横轴是城市人口的年增长速度,竖轴是建设用地的年消耗速度。可以看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城市用地消耗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接受的人口。这就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城市化。所以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城市发展方面,就是要增加人口在城市的聚集程度,同时提供好的公共服务,建设以人为本位的人民城市。
下一步,在城市建成区中特别是沿海的大城市中增加人口密度是必然的。当然,对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关键是要从发展都市圈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不是单一的城市,而是城市集群。未来的发展,中心城区需要控制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郊区城市需要增加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