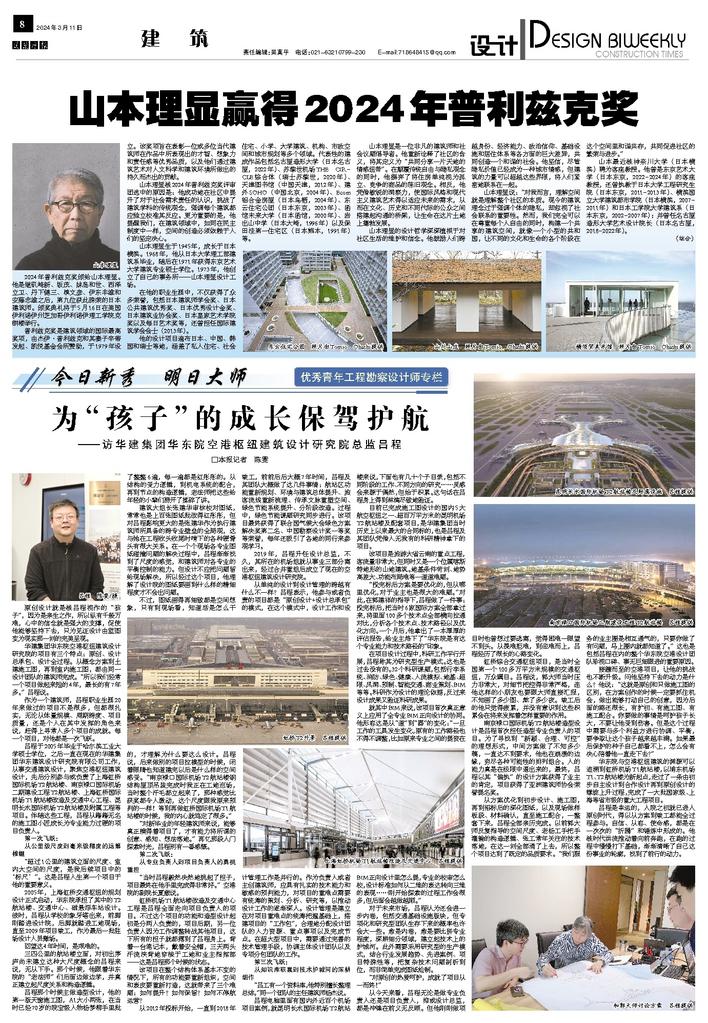□本报记者 陈雯
原创设计就是被吕程视作的“孩子”,因为是亲生之作,所以纵有千般万难,心中的信念就是强大的支撑,促使他能够坚持下去,只为见证设计由蓝图变为现实那一刻的完美呈现。
华建集团华东院空港枢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项目有三个特点:原创、设计总承包、设计全过程。从概念方案到土建施工图,再到室内施工图,都由同一设计团队的建筑师完成。“所以我们经常一个项目做起来短的4年,最长的有7年多。”吕程说。
作为一个建筑师,吕程职业生涯20年来做过的项目不是很多,但都很扎实,无论从体量规模、周期跨度、项目质量,还是个人在其中发挥的角色来说,赶得上寻常人多个项目的成就。每一个项目,对他都是一次飞跃。
吕程于200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之后一直在现在的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从事交通建筑设计,聚焦空港枢纽建筑设计,先后分别参与或负责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2航站楼、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建设工程T2航站楼、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1航站楼改造及交通中心工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T2航站楼及附属工程等项目。伴随这些工程,吕程从籍籍无名的施工图小匠成长为专业能力过硬的项目负责人。
第一次飞跃:
从公里级尺度到毫米级精度的运筹帷幄
“超过1公里的建筑立面的尺度、室内大空间的尺度,是我后续项目中的‘标尺’”。这是吕程人生第一个项目于他的重要意义。
2005年,上海虹桥交通枢纽的规划设计正式启动,华东院承担了其中的T2航站楼、交通中心、磁悬浮车站设计。彼时,吕程从学校的象牙塔出来,前脚刚踏进设计院,后脚就踏进工地现场,直至2009年项目竣工,作为最后一批驻场设计人员撤场。
回望这4年时间,是艰难的。
三四公里的航站楼立面,对初出茅庐尚未建立这种大尺度概念的吕程来说,无从下手。那个时候,他跟着华东院的“老法师”们后面边做边学,并真正建立起尺度关系和构造逻辑。
吕程那个时候主做造型设计,他的第一版天窗施工图,A1大小两张,在当时已经70岁的院宝级人物杨梦柳手里批了整整6遍,每一遍都是红彤彤的。从结构的受力逻辑,到机电系统的配合,再到节点的构造逻辑,老法师把这些给年轻的小辈们掰开了揉碎了讲。
建筑大组长张建华审核校对图纸,常常也是上百张图纸批改得红彤彤,但对吕程影响更大的是张建华作为执行建筑师所具备的跨专业壁垒的全局观,这与她在工程收头收尾时啃下的各种硬骨头有很大关系。在一个个现场各专业图纸碰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吕程渐渐找到了尺度的感觉,和建筑师对各专业的平衡控制的能力。但设计不应把问题留给现场解决,所以经过这个项目,他理解了设计院的图纸要画到什么样的精细程度才不会出问题。
不过,图纸画得再细致都是空间想象,只有到现场看,知道活是怎么干的,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吕程说,后来做别的项目拉模型的时候,闭着眼睛也知道建完以后是什么样的空间感受。“南京禄口国际机场T2航站楼钢结构屋顶吊装完成时我正在工地巡场,当时整个汗毛都立起来了,那种感觉比获奖都令人激动,这个尺度跟我原来预判的一样!等到再做虹桥国际机场T1航站楼的时候,我的内心就笃定了很多。”
“对新毕业的年轻建筑师来说,能够真正摸得着项目了,才有能力将所谓的创意、感知、想法落地。”再忆那段入门探索时光,吕程别有一番感慨。
第二次飞跃:
从专业负责人到项目负责人的勇挑重担
“当时吕程毅然决然地挑起了担子,项目最终在他手里完成得非常好。”空港院的副院长夏葳说。
虹桥机场T1航站楼改造及交通中心工程是吕程全面走向项目负责人的项目。不过这个项目的功能和造型设计起初是分两人负责的,项目后期,另一位负责人因为工作调整转战其他项目,这下所有的担子就都撂到了吕程身上。背着一台笔记本,戴着安全帽,三天两头汗流浃背地穿梭于工地和业主指挥部——这是吕程那个时候的状态。
该项目在整个结构体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所有的功能要重新组织,空间和表皮要重新打造,这就带来了三个难题:如何提升?如何保留?如何不停航运营?
从2012年投标开始,一直到2018年竣工,前前后后大概7年时间,吕程及其团队大概做了这几件事情:航站区功能重新规划、环境与建筑总体提升、旅客流线重新梳理、传承文脉重塑空间、绿色节能系统提升、分阶段改造。过程中,绿色节能课题研究同步进行。该项目最终获得了联合国气候大会绿色方案解决奖第二名、中国勘察设计奖一等奖等荣誉,每年还吸引了各地的同行来参观学习。
2019年,吕程升任设计总监,不久,其所在的机场组就从事业三部分离出来,经过合并重组后成立了现在的空港枢纽建筑设计研究院。
从单纯的设计到设计管理的跨越有什么不一样?吕程表示,他参与或者负责的项目都是“原创设计+设计总承包”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设计工作和设计管理工作是并行的。作为负责人或者主创建筑师,应具有扎实的技术能力和敏感的预判能力,对项目的重难点需要有统筹的策划、分析、研究等,以推动设计工作的逐渐深入。设计管理是建立在对项目重难点的统筹把握基础上,搭建项目的“工作包”,合理地分配设计团队的人力资源、重点事项以及完成节点。在超大型项目中,需要通过完善的技术管理手段,协调主体设计团队以及专项分包团队的工作。
第三次飞跃:
从知识库积累到技术护城河的深耕细作
“吕工有一个资料库,他特别擅长整理总结。”同一个团队的主任建筑师杨杰说。
吕程电脑里面有国内外近百个机场项目案例,就昆明长水国际机场T2航站楼来说,下面也有几十个子目录,包括不同阶段的工作、不同方向的研究……灵感会来源于偶然,但始于积累。这句话在吕程身上得到淋漓尽致地验证。
目前已完成施工图设计的国内5大航空枢纽之一、超百万平方米的昆明机场T2航站楼及配套项目,是华建集团当时历史上以来最大的合同标的,也是吕程及其团队凭借人无我有的科研精神拿下的项目。
该项目是旅游大省云南的重点工程,客流量非常大,但同时又是一个位属喀斯特地形的山地建筑。地基条件苛刻、地势高差大、功能布局难等一道道难题。
“投完标后方案是要优化的,但从哪里优化,对于业主也是很大的难题。”对此,在郭建祥的指导下,吕程做了一件事:投完标后,把当时6家国际方案全部拿过来,将里面100多个技术点全部横向拉通对比,分析各个技术点、技术路径以及优化方向。一个月后,他拿出了一本厚厚的评估报告,给业主烙下了“华东院是有这个专业能力和技术路径的”印象。
在项目设计过程中,科研工作平行开展,吕程称其为研究型生产模式。这也是过去没有的。32个科研课题,包括行李系统、消防、绿色、健康、人流模拟、地基、超限、风洞、预制、智能交通、商业策划、BIM等等。科研作为设计的理论依据,反过来设计成果又验证科研成果。
就其中BIM来说,该项目首次真正意义上应用了全专业BIM正向设计的协同。他形容这是从“道”到“器”的变化:“一旦工作的工具发生变化,原有的工作路径也不得不调整,比如原来专业之间的提资在BIM正向设计里怎么提,专业的校审怎么校,设计标准如何从二维的表达转向三维的表现……刚开始探索的过程工作会很多,但后面会越做越顺。”
对于未来市场,吕程认为还会进一步内卷,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版块,但专项化和研究型团队生存下来的概率也许会大一些。愈是内卷,愈是要比拼专业程度,深耕细分领域,建立起技术上的护城河。此外需要采用研究型的生产模式,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先进案例、项目特殊性等,把复杂技术问题剖析到位,而非简单完成图纸绘制。
“对原创的热爱呵护,成就了项目从一而终!”
从今天来看,吕程无论是做专业负责人还是项目负责人,抑或设计总监,都是冲锋在前义无反顾。但他刚刚做项目时也曾想过要逃离,觉得困难一眼望不到头。从畏难拒难,到迎难而上,吕程经历了很长的心路变化。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是当时全国第一个100多万平方米规模的交通枢纽,万众瞩目。吕程说,郭大师当时压力非常大,对细节把控得非常严格,连他这样的小朋友也要跟大师直接汇报,不知画了多少图、熬了多少夜。竣工后的他只觉得疲累,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积累会在将来发挥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T2航站楼造型设计是吕程首次担任造型专业负责人的项目。为了寻找到“新颖、合理、可控”的理想形式,中间方案做了不知多少稿,一直达不到要求,他也在崩溃的边缘,穷尽各种可能性的排列组合。人的能力真是在极限中逼出来的,最终,吕程以其“偏执”的设计方案获得了业主的肯定,项目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荣誉提名奖。
从方案优化到初步设计、施工图,再到招标后的深化图纸,以及现场做样板段、材料确认,直至施工配合,一整套下来,吕程全部亲历完成。以前郭大师反复指导的空间尺度、老杨工手把手灌输的构造逻辑、张工常年关注的技术落地,在这一刻全部涌了上去,所以整个项目达到了既定的品质要求。“我们服务的业主圈是相互通气的,只要你做了有问题,马上圈内就都知道了。”这也是包括吕程在内的整个华东院空港设计团队珍视口碑、事无巨细跟进的重要原因。
接踵而至的空港项目,让他的挑战也不断升级。问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他说:“这就是原创和只做施工图的区别,在方案创作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做出能够打动自己的创意,因为后面的路还很长,有扩初、有施工图、有施工配合。你要做的事情是呵护孩子长大,不要让他受到伤害。但是这个过程中需要与多个利益方进行协调、平衡,要争取让这个孩子越来越丰满。如果最后保护的种子自己都看不上,怎么会有决心陪着他一直走下去?”
华东院与空港枢纽建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虹桥机场T1航站楼,以浦东机场T1、T2航站楼为新起点,走过了一条由初步自主设计到合作设计再到原创设计的螺旋上升过程,完成了一大批国家级、上海等省市级的重大工程项目。
吕程是幸运的,入院之初就已进入原创时代,得以从方案到竣工都能全过程参与。自信、从容、使命感,都是在一次次的“折腾”和锤炼中形成的。他被时代洪流推动着向前奔跑,在跑的过程中慢慢打下基础,渐渐清晰了自己这份事业的轮廓,找到了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