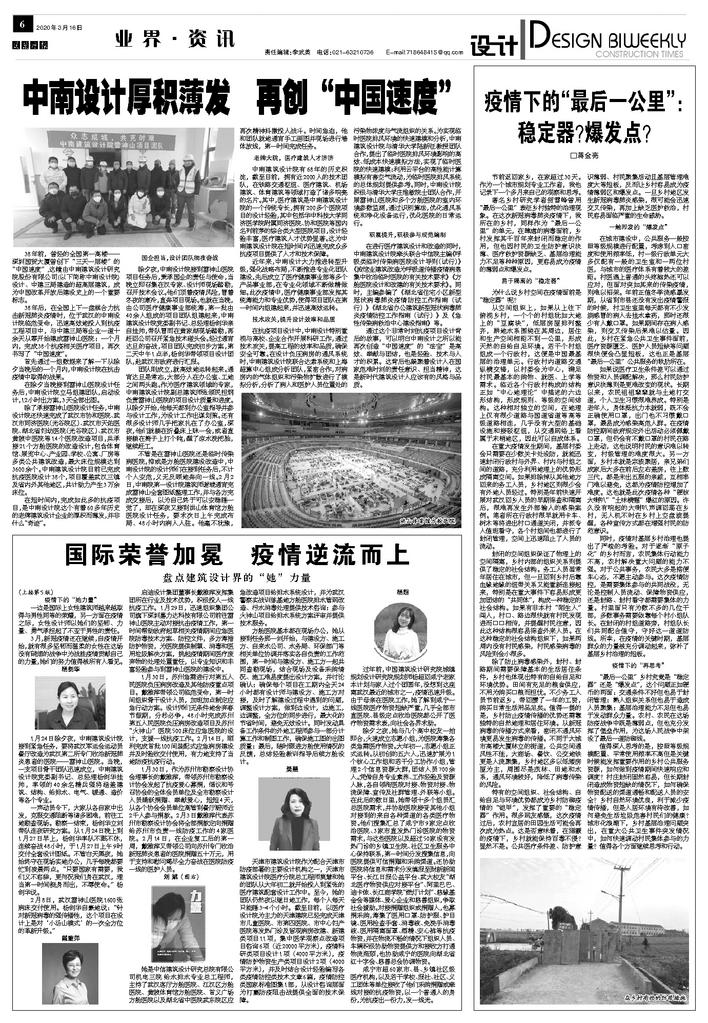节前返回家乡,在家超过30天。作为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工作者,我也记录下一个多月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著名乡村研究学者贺雪峰曾用“最后一公里”表征乡村独特的治理现象。在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我所在的乡村,同样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单元,在肆虐的病毒面前,乡村发挥其千百年来封闭而稳定的作用,但也因村民的卫生防护意识淡薄、医疗救护资源缺乏、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种种原因,更容易成为疫情的薄弱点和爆发点。
易于隔离的“稳定器”
为什么说乡村空间在疫情面前是“稳定器”呢?
从空间组织上,如果从上往下俯视乡村,一个个的村组犹如大地上的“豆腐块”,低层房屋排列整齐,耕地水系围绕在其周边,居住和生产空间相距不到一公里,形成天然的自给自足环境。若干个村组组成一个行政村,这便是中国最基层的治理单元。行政村内道路交通纵横交错,以村委会为中心,满足村民最基本的购物、就医、上学等需求。临近各个行政村构成的结构正如“中心地理论”中描述的六边形结构,形成规则、等级的空间结构。这种相对独立的空间,在地理上仅有很少道路与国道省道等高等级道路相连,几乎没有大型的基础设施和接驳枢纽,从交通网络上看属于末梢地区,因此可以自成体系。
在重大疫情发生期间,基层村委会只需要在少数关卡处设防,就能迅速封闭行政村与外界、村内与村组之间的道路,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形成隔离空间。如果排除掉从其他地方回来的务工人员,乡村地区则很少会有外地人员经过。特别是年前快速开展对武汉回乡人员的早期筛查和隔离后,很难再发生外部输入的感染案例。笔者所在行政村很早就用卡车、树木等将进出村口通道关闭,并派专人值班看守,各个村组间也都进行了封闭管理,空间上迅速阻止了人员的流动。
封闭的空间组织保证了物理上的空间隔离,乡村内部的组织关系则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务工人员虽常年居住在城市,但一旦回到乡村后靠血缘地缘的纽带关系又能重新连接起来,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下容易形成更加团结的“共同体”,构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如果有非本村“陌生人”闯入,村口、路边很快就有村民发现进而口口相传,并提醒村民注意,因此这种结构很容易筛查外来人员。在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组织下,如果两周内没有村民感染,村民感染病毒的风险则会小很多。
除了防止病毒感染外,封村、封路期间需要保障基本的生活居住条件,乡村也体现出特有的自给自足和环境优势。田间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不用为购买口粮而担忧。不少务工人员节前返乡,带回攒了一年的工资,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足矣。值得一提的是,乡村防止疫情传播的优势还需靠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居住环境。从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来看,密闭不通风环境更易发生病毒的传播。不同于大城市高楼大厦林立的街道,公共空间通风性不佳,大商场、餐饮、公交地铁更是人流聚集,乡村地区多以低矮房屋为主,周围尽是茂林、田地和水系,通风环境较好,降低了病毒传染的风险。
特有的空间组织、社会结构、自给自足与环境优势都成为乡村防御疫情的“铠甲”,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很多网友感慨,这次疫情过后,农村宜居的田园生活可能会再次成为热点。这是否意味着,在猖獗的疫情下,乡村就能保持百毒不侵?显然不是。公共医疗条件差、防护意识薄弱、村民聚集活动且基层管理难度大等短板,反而让乡村容易成为疫情薄弱区和爆发点。一旦乡村地区发生新冠病毒肺炎感染,很可能会迅速交叉传染,再加上缺乏医护救治,村民容易面临严重的生命威胁。
一触即发的“爆发点”
在城市建设中,公共服务一般按照等级规模进行配置,考虑到人口密度和使用频率低,村一级行政单元大多仅配有一般的卫生室和一两位村医,与城市的医疗体系有着较大的差距。村医遇上普通的头疼脑热还可以应对,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疫情,则难以招架。年前正值冬季流感暴发期,从省到市县还没有发出疫情警报的时候,村卫生室里每天都有不少发烧感冒的病人去挂水拿药,那时还很少有人戴口罩。如果期间存在病人感染,则交叉传染后果难以估量。因此,乡村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医疗资源匮乏、医护人员短缺等问题很快便会凸显短板,这也正是基层“最后一公里”公共服务的软肋所在。
如果说医疗卫生条件差可以通过物资和人员调配解决,那么村民防护意识淡薄则是更难改变的现状。长期以来,农民祖祖辈辈就与土地打交道,个人卫生习惯很难养成。特别是老年人,身体抵抗力本就弱,既不会正确使用口罩,出门也不习惯戴口罩,最易成为感染高危人群。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规定外出活动必须佩戴口罩,但仍会有不戴口罩的村民在路上走动,这也说明村民的意识难以转变,村级管理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乡村本就是宗族聚居,亲兄弟们成家后大多在前后左右盖房,往上数三代,都是未出五服的亲戚,互相串门难以避免,这都为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这也就是此次疫情各种“硬核大喇叭”“土味横幅”爆红的原因。许久没有响起的大喇叭声调回荡在乡村,无人机不时在乡村上空盘旋提醒,各种宣传方式都在增强村民的防范意识。
同时,疫情对基层乡村治理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逐渐“原子化”的乡村而言,农民集体行动能力不高,农村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不强。对于公共事务,农民大多是搭便车心态,不愿主动参与。这次疫情防控,是需要集体参与的共同战役,无论是控制人员流动、保障物资供应,还是封路、封村看守都需要集体的力量。村里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干部,多数事务需要依靠每个村小组队长。在封闭的村组道路旁,村组队长们共同配合值守,守好这一道道防线。所幸,在疫情的关键时期,基层群众的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弥补了基层乡村治理的短板。
疫情下的“再思考”
“最后一公里”乡村究竟是“稳定器”还是“爆发点”,这个问题正如硬币的两面:交通条件不好但也易于封闭管理;熟人组织关系但也易于造成人员聚集;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但也易于发动群众力量。农村、农民在这场防疫战争中既是薄弱点,但也充分发挥了堡垒作用,为这场人民战争中架设了最后一道防御线。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按照等级规模配置、平常使用频率不高但是关键时候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乡村公共服务资源,如何做到疫情期间快速响应和调度?村庄封闭固然容易,但长期封闭造成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如何确保物资配送的渠道通畅和配送人员的安全?乡村自然环境优良,利于减少疫情传播,但是人居环境有待改善,如何避免生活垃圾危害村民们的健康?城市化浪潮下,乡村基层治理问题突出,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情况中,如何快速调动村民集体参与的力量?值得各个方面继续思考和行动。
在乡村有效的防疫措施